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有两件万历时期洒线绣方补,其中一件(图3)纵38厘米,横37厘米,红色的地纹上两条盘旋而上的金龙在云间隔河相望,波光粼粼的银河上架有一座白玉栏杆石桥。一金龙的斜上方饰有连成菱形的四颗星星,代表织女投给牛郎的四个梭子;另一金龙的斜上方饰有等边的三颗星星,代表牛郎投给织女的牛拐子。在两龙上端的云气里,两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遥遥相望,代表牛郎、织女各住一方。整个补子的图案虽没有直接出现牛郎、织女的形象,却用银河、星星、宫殿代表了鹊桥相会的情景,很是巧妙。
重阳景菊花补子:九月初九重阳节,在民间有登高的习俗,所以重阳节又称“登高节”。这一日人们出游赏菊,登高望远,并饮菊花酒。宫中亦有赏菊、登高、饮菊花酒的传统。重阳景菊花补子服自九月初四日便开始穿着。
阳生补子:古人认为,冬至过后,阴气逐渐下降,阳气开始上升。阳生补子用于冬至节。由于羊与“阳”谐音,在补子上用口吐瑞气的羊作为图案,谐音“阳生”,预示冬去春来。
另外,在留存的实物中除了上述应景补子,还见有秋千补子、玉兔补子(定陵出土)。刘若愚在《酌中志》记有“清明,则秋千节也,带杨枝于鬓。坤宁宫后及各宫,皆安秋千一架……”“八月宫中赏秋海棠、玉簪花……至十五日,家家供月饼、瓜果,候月上焚香后,即大肆饮啖。”虽未明确写出清明节、中秋节要穿应景补子服,却详细记述了所用应景之物,因此这两种补子可能为《酌中志》所漏记。
二、应景补子的使用者
《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中记载:“七夕,暑退凉至,自是一年佳候。至于曝衣穿针、鹊桥牛女,所不论也……今内廷虽尚设乞巧山子,兵仗局进乞巧针,至宫嫔辈则皆衣鹊桥补服,而外廷侍从不及拜赐矣。”说明宫嫔可以着应景补服。
在《酌中志》“贴里”条目记:“司礼监掌印、秉笔、随堂、乾清宫管事牌子、各执事近侍,都许穿红贴里缀本等补,以便侍从御前。……自正旦灯景以至冬至阳生,万寿圣节,各有应景蟒纻。自清明秋千与九月重阳菊花,具有应景蟒纱。”说明部分御前宦官是可以缀补子。虽记述的应是代表等级的补子,但是根据穿着应景题材“贴里”的记载,缀应景补子也是极有可能的。而后,在《饮食好尚纪略》中提及各类应景补子时,明确记载除“宫眷”外,还有“内臣”可以穿用。
在定陵出土文物中,皇帝所缀补子均为云龙纹或龙戏珠纹,未见应景补子。而孝靖、孝端皇后棺内除了云龙纹、龙凤纹、凤穿花纹补子,还有吉祥图案、文字补子及应景的艾虎五毒补子。这也与《酌中志》中所记相符。
综上所述,应景补子应是后宫宫眷、宦官内臣在一些传统节气时衣服上所缀的补子,以示顺应天时,祈求平安。
三、应景补子的穿着方式
除《酌中志》外,明代史料中很少有提及“应景补”的,仅在《舆服志》所记皇后常服中“鞠衣”条目有“鞠衣红色,胸背云龙纹”的记述,但是否包括应景补子,尚不得而知。
在定陵出土文物中,据《定陵》一书记,女衣共134件,分别出自孝端、孝靖两后的棺内。这些女衣均为对襟,立领、方领或圆领,大袖,绝大部分在前胸和后背缝有方补,前胸左右襟各一块,后背一块。方补多为绣制,少数为缂丝。纹饰以云龙纹居多,其次有龙凤纹、凤纹、花卉纹,再有万寿、洪福齐天等福寿吉祥文字。也包括了上述提及的艾虎五毒纹方补。可以看出,女装补子(包括应景补子)都是缝于女上衣。而这种女衣则不属于礼服范畴,乃为常服。
责编 有仪
来源:《收藏》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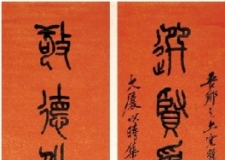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蔡祖逖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蔡祖逖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高明柱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高明柱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吴广华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吴广华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刘玉栋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刘玉栋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王金录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王金录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刘凤仙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刘凤仙 “意在画外o赵青仲画展”亮相燕京书画社
“意在画外o赵青仲画展”亮相燕京书画社 艺科融合 青春宣言|清华美院2025届本科生毕业作品展开幕
艺科融合 青春宣言|清华美院2025届本科生毕业作品展开幕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杨志谦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杨志谦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喻寿奇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喻寿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