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上海图书公司所存善本碑帖中,尚有陈淮生旧物数种,颇多精好者。如北魏《刁遵墓志》,系清乾隆中所拓“雍”字初损本,其第五行“金紫左光禄大夫建平”之“夫建”二字、第九行“所见者”之“所”字等,虽皆有漫漶但均可辨认;十二行“见而异之”之“异”、“太和中”之“和”,十三行“洽德于民”之“民”、“正始中征为太尉高阳王谘议参军”之“正始中”诸字,亦皆完好。虽非康(熙)雍(正)间出土时最初之拓,但仍属珍稀。其后有民国间金石名家易大厂题跋,述其壬戌(1922年)在津沽夜访陈氏时初见此本,“近灯延赏,遂我平生”,以及至丁卯(1927年)新岁再获重睹并作跋之种种,生动传神,佚闻隽永。又如隋《李氏女尉富娘墓志》,据说清同治间出土后不久,即有碑贾覆刻;后又被人以覆刻志盖配原刻志石,再以原刻志盖配覆刻志石分售,遂致混淆。所传志石,以庞芝阁、李山农两家所藏为最著名,而其真伪,仍有争议。上海图书公司本即为庞氏藏石本,有陈淮生戊辰(1928年)五月自跋。
更值得一说的,是陈氏旧藏《董美人墓志》,先后有褚德彝庚申(1920年)及丁卯(1927年)、吴湖帆戊辰(1928年),以及赵尊岳己巳(1929年)诸跋,皆文词典雅,精楷工书,而吴氏所记其与陈氏之金石佳缘,尤具意味:
丁卯冬,淮生道兄携示隋《常丑奴墓志》,与余藏冬心斋本相校勘,赏析竟日,各易题字,以识石墨胜缘。余并示以《董美人志》,意亦欲共观,而先生亦以此册未携为怅。盖《丑奴》《美人》,俱隋志中铭心绝品、仅有之本也,吾二人俱双有之,岂非奇缘?戊辰冬日,访先生于寓斋,因得饱眼福,并属余录郑小坡题西河词及余和词于后。
褚德彝丁卯跋末页边,有陈淮生题记,似可与吴氏所记并读:“往在燕都,得此志并《常丑奴志》于伦邸,曾以《美人》《丑奴》名室。一时游戏,不足据为典要,姑誌于此。己巳人日承修。”又今已归上海图书馆的吴湖帆旧藏《董美人墓志》浓墨剪裱本册后,有“丁卯冬日武进赵尊岳闽县陈承修同观”款,也正是当年陈淮生等在吴氏处的共赏之记。陈淮生名承修,闽县人。嗜金石,精鉴赏。罗振玉《石交录》卷一有关汉熹平石经条下,曾附记其人其事:“岁戊辰,闽中陈君淮生承修,拟向诸家集拓,旋南归不果,乃由大兴孙君壮成其事……淮生旧为学部同僚,好古甚笃,虽处浊乱之世,其行己尚有所不为,晚近佳士也。乃中寿物故,予最后集录,彼竟不见, 为可憾也。”而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所刊吴湖帆《梅景书屋题跋记》(佘彦焱整理)中,有“汉马姜墓碣”题记,谓:“新出土汉墓志只此一种,闻石尚存罗雪堂丈处。此拓乃故友陈淮生贻我者,越淮生之殁,已一年矣。(癸酉冬至)”因知陈氏之卒,当在1932年(壬申)。吴氏跋其自藏明拓唐《梁文昭公房公碑》中又记:“此本余易得于闽友陈淮生。淮生知余有昭陵古拓之好,专相让也。今淮生又作古人,对此能不怃然。癸酉中秋,校竟题此。”癸酉为1933年,至庚辰(1940年)秋跋自藏旧拓唐《高唐公马周碑》残本时,犹忆:“此册为吾友陈淮生先生旧物,昔岁赠余者。今阅先生之殁将十年,曝碑检阅,如遇故人,因记。”则两人金石之交,可见一斑。
其他还有如吴昌硕题跋明拓《石门颂》,固始张(傚彬)氏旧藏明中期拓《礼器碑》等,都是上海图书公司所藏碑帖中的名品。而所有这些流传有绪、见证着一代又一代藏家和同好们研究赏玩、品评交流,乃至翰墨因缘、趣闻佚事的珍稀善本,历经岁月沧桑、人事曲折之后,又陆续汇聚上海图书公司,不仅因各自独到的文物价值,给之前的库藏积累添宝;更由托物寄意的前辈遗韵,为今日之传承弘扬增色。展对佳拓,摩挲细阅之下,不禁想到:1985年在上海图书公司重新开业的艺苑真赏社,民国间曾与神州国光社、有正书局、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上海中华书局等,皆以碑帖影印著称。倘能继此传统,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业已开始的影印唐柳公权《玄秘塔》、宋拓孤本《兰亭续帖》、《郁孤台法帖》、《凤墅帖》、宋拓汉《嵩山太室石阙铭》仿真限量本,以及《中国历代法书墨迹大观》(全十八册)等数百种碑帖的基础上,全面规划,精益求精,将长期深藏的善本碑帖,更有系统、更高质量的影印流布,则无论于金石或学术,皆堪称功德无量,影响远大。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蔡祖逖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蔡祖逖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高明柱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高明柱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吴广华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吴广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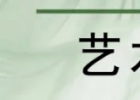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刘玉栋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刘玉栋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王金录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王金录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刘凤仙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刘凤仙 “意在画外o赵青仲画展”亮相燕京书画社
“意在画外o赵青仲画展”亮相燕京书画社 艺科融合 青春宣言|清华美院2025届本科生毕业作品展开幕
艺科融合 青春宣言|清华美院2025届本科生毕业作品展开幕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杨志谦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杨志谦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喻寿奇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喻寿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