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光寺自建寺以来,始终受到军政界、文化界名人的青睐。清乾隆时期的名将岳钟琪、钦差大臣向荣、四川总督丁宝桢、闽浙总督杨国桢,道光时期的军机大臣潘世恩、四川按察使黄云鹄、四川总督裕瑞、成都副都统庆云,民国时期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等,或曾向宝光寺送过匾额,或是留书以赠。清代著名书法家赵熙、包弼臣、龚晴皋、王懿荣、刘月渔,画家朱景云、石中坚、江兆筠等,也曾慷慨捐送自己的作品。进入现代,更多文化名人过访此地,如于右任、张大千、徐悲鸿、谢无量、娄师白、巴金、艾芜、冯建吴、张采芹、董寿平、徐无闻、赵蕴玉、马识途、范曾、廖静文等,他们在寺院留下的作品,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文化价值。寺内还藏有张大千胞兄、著名画家张善孖1926年诗稿手本,是研究民国时期四 川地区文化风 貌的重要文献资料。
民间捐赠
寺院各方信众为捐献功德,或出资请名人作画,或购买传世画作,或将祖传藏品捐赠寺院,这类藏品是宝光寺收藏的另一重要来源。如张大千1941年所临榆林窟壁画《水月观音图》,融合传统国画与西洋技法,银钩铁线,青绿重彩,瑰丽难匹,画成后即震惊当世。后经时任四川省主席张群批示,新都邦人士女联合集资,于1945年以巨资购入请进宝光寺,从此成为寺内铭心绝品,被奉为至宝。传为宋徽宗《白鹦鹉图》、赵孟《五马图》、慈禧太后《绿牡丹图》,都是清末游历外省的新都人重金购回,后来由其子孙无偿捐予寺院,这几幅作品虽为后人仿作,然古意盎然,品质不俗,时隔百余年后也成了不可复得的重要文物。再如明代陈遵《荷花双燕图》、清代李吉寿与李洵叔侄的真迹、陈廷璧《瑞应麒麟图》等,都经由类似的渠道进入寺院。其中《瑞应麒麟图》一幅,虽为道光年间仿明代宫廷绘画,却很好地保存了原作的风采,尤其照录了原画中沈度的长篇题记,为今人研究明代中非关系史保存了一段重要文献资料。
寺内还收藏有大量历代祖师影像、宗教人物画、水陆道场画,如《地狱十殿图》《佛三世图》《密宗明王人物图》《破山海明禅师画像图》《光公老和尚图》《佛德和尚图》《道帆心公和尚图》《照峰和尚图》等,均为当时文人画家或民间画工所绘。这类画作虽然多数都没有留下作者姓名,却是研究清末人物肖像画和佛教艺术的重要资料。
寺内净土院中有念佛堂,堂中舍利塔后有巨幅彩绘壁画《释迦涅槃图》。壁画高达3米,宽4米有余,以典雅高贵的色泽,描绘了佛人涅槃时众人举哀的场景。壁画构图以对称为主,谋求局部变化。人物形貌端严,衣褶飘带合乎法度,作风谨严,虽取自佛经,亦掺入诸多世俗趣味,具有相当高的文化艺术价值。此图在民国年间重绘过,1997年四川省文物考古所揭裱重修,基本保持了原画的面貌。此画是目前四川境内禅寺中为数不多、保存较好的清代彩绘壁画。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寺内重修藏经楼,在楼上两边墙壁上彩绘十八诸天,沥粉贴金,光彩耀目。图像至今保存完好,与念佛堂《释迦涅槃图》一起,并称寺院壁画双璧。
僧人自作
自清初重兴,宝光寺不少僧人对绘画书法情有独钟,且艺术造诣颇为可观,如照峰和尚、佛贞和尚、贯一法师、自信和尚、云晏法师、遍能法师等,都各有擅长。贯一和尚1921年任宝光寺方丈,精于佛学,博通文史,喜诗文,好书法。楷书以颜、柳为宗,颇具法度;隶书从汉魏入手,用笔放纵而不越规矩;尤善榜书,笔墨酣畅,气势磅礴。遍能法师早年师事清末翰林、蜀中名士赵熙,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底蕴。他精于文物鉴赏,又是书法名家,其书法端庄而不板滞,灵便而不轻浮,往往令一般浅涉墨翰而侈谈神气韵味者望尘莫及。此外,一些与宝光寺常有交往的川内高僧,也在宝光寺留有作品,如乘三法师擅长行书,如蜻蜓点水,脱略恣逸;隆莲法师善行楷,端庄平正,温文尔雅。这些具有深厚文化功底的僧人不仅留下了自己的创作,还致力于从各方收集作品,经数代的努力,终使宝光寺的书画收藏蔚为大观。这批藏品,其意义不止于书画艺术本身,更是僧人文化修养与艺术才能的见证,足见宝光寺既是经声萦绕的佛土,又是翰墨流香、丹青映彩之地。
宝光寺所藏书画上迄元代,下至近现代,既包含大量蜀地名作,也有来自南粤、京津、湖广各地的名家作品,可谓时接千载,荟萃南北。书法方面,包括各类佛经、诗词、札记、对联,往往深含佛教义理。绘画方面,多为人物花鸟。人物多为佛教题材,有祖师像、历代高贤隐士图;花鸟多梅、兰、竹、鹤之类。无论书法还是绘画,既有显而易见的佛教色彩,又深具中国水墨艺术之美。
宝光寺的收藏能拥有今天的成就,缘于寺僧和信众代代传承的香火与善缘。佛家视万物平等,无尊卑贵贱之分,也正是此平常之心,成就了它保存文化的功业。宝光寺的书画收藏有两大特点:一是不局限于金钱价值与作者名望。无数名不见经传的画家和民间画工的作品,甚至佚名的书画作品都得以入藏。这样的收藏,恰能补典籍史书之缺,使后世得以领略一个时代艺术风貌的丰富性。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藏品有的因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成为珍品,有的则因其文化价值与史料价值而成为不同于经典名家之作的另一个宝藏。另一个特点是不局限于时代远近。当代人的作品,即使为普通人所作,但凡有缘入寺,都被僧众郑重对待。这两个特点,使寺院收藏不同于一般世俗收藏重经典轻日常、重古代轻当下的传统,却暗合现代博物馆的两大收藏理念——一是文化经典与反映日常生活的文物并重;二是为了历史,收藏今天。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寺院收藏并不只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而是对世俗收藏必不可少的补充。宝光寺的书画藏品正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宝光寺书画收藏,除得益于寺僧的文化功力与精心藏护之外,也受惠于知识阶层、显贵要人、民间社会三方面的共同支持维护,以及佛教界同人的襄助。这体现了新都各界对宝光寺的信任与尊重,也体现了艺术的魅力不仅可以超越时空,也可以消除人心的隔膜与鸿沟。恰是各界人士对文化、宗教和艺术的这一份尊崇与礼重,使得新都在世事并不安稳的近现代却依然能够葆有宝光寺的经声香火,依然能够养成人文荟萃之地。
时光荏苒,宝光寺文物收藏事业在20世纪末迎来了新的发展。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视察宝光寺时指示僧众加强文物保护,“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指示驻军对宝光寺加以保护。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为宝光寺题字“文物重地”,以后宝光寺又接待了多位中央领导人,都对寺内文物收藏大加赞赏,并提议修建陈列馆进行展览。20世纪80年代,遍能法师出任方丈,主持清理文物,修建文物库房,实施园林建设规划。90年代初,寺内僧众首次对文物字画进行了全面整理清点,将库房北厢改建为崭新的文物库房。2001年5月,宝光寺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8月25日,在清代云水堂旧址兴建的文物精品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是国内第一个由寺院修建的文物博物馆,其硬件设施完全达到了现代博物馆的陈列要求,开寺院文物收藏展览之先河。自此,宝光寺书画藏品得以走出重门深殿,在更大的范围内惠及世人。
来源:《收藏》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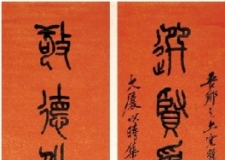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蔡祖逖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蔡祖逖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高明柱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高明柱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吴广华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吴广华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刘玉栋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刘玉栋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王金录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王金录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刘凤仙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刘凤仙 “意在画外o赵青仲画展”亮相燕京书画社
“意在画外o赵青仲画展”亮相燕京书画社 艺科融合 青春宣言|清华美院2025届本科生毕业作品展开幕
艺科融合 青春宣言|清华美院2025届本科生毕业作品展开幕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杨志谦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杨志谦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喻寿奇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喻寿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