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阳涧磁定窑遗址
定窑创烧于何时,是隋代或唐初,还是唐中晚期,是官窑,还是民窑,贡御时间有多长,工艺的改进和创新情况,元代定窑的概貌,时至新世纪尚无确切的定论,为了解决这些学术课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2009秋冬之季,对定窑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本次发掘在4个地点布方21个,加上遇到遗迹进行的扩方面积,发掘总面积776平方米,出土了丰富的遗迹遗物,清理各类遗迹94处,其中窑炉11座、作坊12座、房基3座,灰坑45个、灶7座、墓葬2座、沟6条、界墙8道,出土了数以吨计的各时期的瓷器和窑具,其中完整或可复原标本数千件,这些出土的标本中不乏以往我们认识的定窑精品,也有一些以前未曾见过的独特器物,揭开了定窑的历史谜团,因此被评为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考古发现并清理了从中晚唐到元代各个时期的地层,自中晚唐到金末,定窑一直盛烧,到元代继续烧造。因此文化层很厚、很丰富,从2、3米到8、9米不等。其中以往从其他考古材料并不十分了解的中晚唐、北宋中期和元代地层的清理,为我们全面了解定窑的生产历史和工艺发展的全过程提供了详实的资料。金代的文化层普遍很厚,出土物丰富,说明金代是定窑瓷器烧造历史中生产规模最大的时期,但是,器物的质量比北宋时期有所下降。
大体可以判定定窑的始、终烧时间,我们在不同发掘地点的8、9个探方中发现了晚唐、五代到宋初的地层,其下即为生土,并出土有中唐时期特征的碗、执壶残片等,这种反复出现的事实使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定窑的创烧时代在中晚唐时期,早不过中唐。以往关于定窑的创烧时间有初唐和隋代说,都还缺少考古依据。又通过对燕川附近的野北、杏子沟等地的地面调查,发现了大量的元代遗物,可知定窑在元代烧造规模仍较大,但产品质量下降,与宋金时期的精美定瓷已相差甚远。
出土了一批代表定窑各时期贡御情况的重要遗物,如五代、宋初地层中的“官”字款器物,北宋地层中的带“尚食局”、“尚药局”、“乔位”款,装饰龙纹的器物,金代地层中的“尚食局”,“东宫”款盘等。宋金时宫中设立六尚局为宫中服务,“尚食局”“尚药局”是其中的两个,“东宫”则是当时太子的宫殿,说明自五代、历宋至金代,定窑都在为宫廷烧制瓷器。这些带款识的器物多为贡御的器物,考古发现生产这类器物的地点在定窑遗址中分布比较普遍,其中以涧磁岭地区产品质量最高,器物种类最丰富。但即使是在集中出土这些官用器物的地点,也还同时生产胎釉粗劣,制作草率的另一类产品。由此推测这种官作制度似乎是由许多水平较高的窑户承造官用的精致产品,同时其还从事商品生产的体制(秦大树《定窑的历史地位及考古工作》,《中国定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第269页)。
北宋中期以后,窑炉燃料用煤,火膛发现有烧过的煤渣,定窑同时也是北方地区最早采用煤为燃料烧瓷的窑场,印证了定窑创新了烧制工艺,发明了覆烧工艺。定窑生产薄胎瓷器,就必须努力克服烧成中器物变形的问题,所以定窑发明了覆烧工艺。定窑的发掘不仅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瓷器,同时也出土了大批量的不同形状的碗形支圈和环形支圈,用碗形支圈和环形支圈承托器物的口部入窑烧制即采用覆烧工艺,这种工艺首先解决了器物变形的问题,同时也由于覆烧的装窑密度大于一般的叠烧,特别是匣钵单烧,因此极大的提高了产量,有学者统计,采用覆烧工艺可以使瓷器产量比匣钵单烧方法提高4倍左右(刘新园《景德镇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初步研究》,《考古》,1974年06期,24-31页)。在定窑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支圈,特别是在涧西区和燕川区,有堆积如山的支圈窑业堆积。定窑发明的覆烧工艺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对整个瓷器业生产的繁荣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定窑是我国宋金时代北方生产规模最大、影响最广、贡御时间最长的瓷窑场,是中国古代白瓷生产中最具代表性的杰出窑场。白瓷的产生是中国古代瓷器产生和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1998年,1-9页),对世界文明史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在白瓷的发展史中,定窑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综观定窑的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定窑遗址无疑是一座宝库,一座丰碑,它沉淀并代表着一项创造性的天才杰作和独特的艺术与美学成就。
来源:《文物天地》2014年9月刊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蔡祖逖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蔡祖逖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高明柱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高明柱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吴广华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吴广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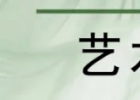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刘玉栋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刘玉栋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王金录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王金录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刘凤仙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刘凤仙 “意在画外o赵青仲画展”亮相燕京书画社
“意在画外o赵青仲画展”亮相燕京书画社 艺科融合 青春宣言|清华美院2025届本科生毕业作品展开幕
艺科融合 青春宣言|清华美院2025届本科生毕业作品展开幕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杨志谦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杨志谦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喻寿奇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喻寿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