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家具“观赏面法则”的五个层面
从一个规范的香几到“用途不明”之物的全程,这正是它令人玩味的妙处所在。无疑,它是独特的个例,但又符合普遍规律。整体而言,明清家具发展的全程呈现出一种规律和规则,笔者称之为“观赏面法则”。定义是各门类的明清家具随着时间推移,每发展一步,观赏面都会出现增益性的变化。从明晚期开始到清早期、清中期、清晚期直至清末民国,硬木家具的发展链上,这种变化从未中断。这一法则有着五个层面的表现:
第一个层面:增加光素木质构件的组合,使家具线型形态逐渐趋近于面型形态。例如以垛边加宽、加厚立面,以攒接、斗簇组成图案等。为光素期的常用手段,雕刻工艺兴起后,逐渐式微,清中期后,悄然退场。
第二个层面:光素构件上增加雕镂。雕饰初萌时期,光素器物上普遍性地增加雕镂,之后刻画日趋纷繁。
第三个层面:加大构件尺寸。具体情况可分两类:第一类是可雕饰的构件面积逐渐加大。典型表现为罗汉床围板加高、桌椅床矮束腰加高、各类牙板加宽、牙头加肥,挂牙和花牙加大等;第二类是有视觉装饰意味的光素构件尺寸加大。
第四个层面:增加构件。亦可分为两类:其一、增加木质装饰构件,例如各式雕饰的花牙、挂牙、牙板以及案子足间挡板逐渐增多。以玫瑰椅为例,体现在靠背增加竖棂、横枨或券口式牙条,日趋丰满,最后变为全板式靠背;其二、器物上增加不同材质构件,如镶嵌大理石、瘿木、铜饰件等,更晚时期,镶嵌瓷板、玉件、剔漆件、铜制珐琅板等,不一而足。
第五个层面,明式变为清式,一系列清式家具出现。
当原式样阻碍观赏面效应发展时,原造型和结构便被改变,典型表现是由清早期开始、清中期勃兴的式样大革命,明式家具演变为清式家具:一、屏风式扶手椅,雕刻空间极大,后来取代了背板窄小的圈椅、四出头椅、南官帽椅、玫瑰椅;二、横向结构架格增加围栏、竖墙、抽屉、柜门,破坏原有式样,成为多宝阁;三、外来的独梃圆桌,由于具有三百六十度立体的观赏面效果,与当时的审美风尚吻合,受到包括内廷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青睐,直至民国时期,一直屹立不倒;四、为适应器物腿子和牙头、牙板上雕刻图案线条的垂直、水平和对称,侧腿淡出,桌、案、几等器物腿部演变成九十度角垂直状。流风浸淫,以侧腿为主要特征的圆角柜(A字柜)悄然消失。
“观赏面效应”背后的推动力量
在硬木家具系统中,“观赏面法则”的效力,安排着家具面貌之变,长期一以贯之。不但壮大着家具的雕饰,且改变着式样和结构,不单是小打小闹的改良,也有推倒再来的革命。观赏面法则的底蕴是其艺术和审美自身的规律,同时也受到各个时期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的支持或制约。它背后的决定力量,一是匠师职业上争雄逞强的心理,二是市场的奖励机制,那些“人无你有、人有你多、人多你好、人素你华”的器物,一定是消费者的宠儿。尤其是黄花梨、紫檀这类奢侈物,市场尤其青睐那些富丽华美、新奇相竞的制品。
那么,可否从理论上解读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外古今艺术理论中,不难找到相关的阐释。如文学研究方面,南朝梁萧统曾在《文选》序中提出了“盖踵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踵,继承。华,光彩。“踵事增华”说的是文章发展的规律,认为文学发展的普遍形态,是由质朴走向华丽,由简洁趋向繁复。它指出了一种文学发展的普遍态势,后来成为对于事物变迁发展的一种基本概括,是世间诸多事物形态和审美走向的抽象总结。用于解释明式家具,似乎也颇有意义。
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认为此类现象是由“名利场逻辑”导致的。他觉得“成为名利场特征的东西正是这场‘看我的’竞赛易变性”、“在名利场上有些优美的结构物,它们是由想战胜比邻的欲望而产生的,同样,在艺术中也有一些伟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当然是艺术家想与同行们竞争,并且要超过他们中的皎皎者的欲望而促成的。”[2]
注 释>>>
〔1〕王世襄,《明式家具的“品”与“病”》,《明式家具研究》,三联书店,2008年。
〔2〕英国 贡布里希著,范景中等译《理想与偶像》100~101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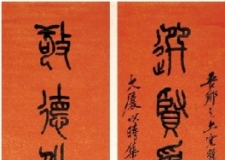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蔡祖逖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蔡祖逖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高明柱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高明柱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吴广华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吴广华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刘玉栋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刘玉栋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王金录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王金录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刘凤仙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刘凤仙 “意在画外o赵青仲画展”亮相燕京书画社
“意在画外o赵青仲画展”亮相燕京书画社 艺科融合 青春宣言|清华美院2025届本科生毕业作品展开幕
艺科融合 青春宣言|清华美院2025届本科生毕业作品展开幕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杨志谦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杨志谦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喻寿奇
《人民艺术》—— 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丨专访喻寿奇


